50岁男人:“你都28了又不是处女,下身碰99次而已,装什么清纯”
50岁男人:“你都28了又不是处女,下身碰99次而已,装什么清纯”
这是刘玥独自待在出租房的第三天了,也是她失去工作的第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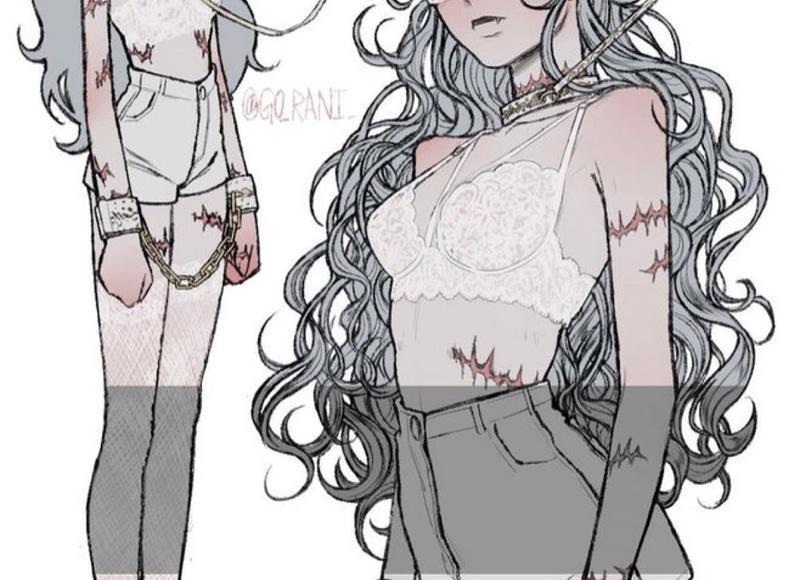
三天前,是年会。老板为了达到团建效果,增加公司凝聚力,设计了一个“男女员工一起挤气球”的项目。一男一女,两个人,手被绑在身后,下半身撅起,像乞食的弟鸭,去挤俩人中间那个鼓胀的气球。气球的颜色是红的,地上的灯光透过气球照过来,染红同事们的脸。到她了,她的对面是部门的主管,那个大腹便便,明明有妻有子,还多次对她咸猪手的男人。
男人站到她对面的时候,对她猥琐地笑。肥厚的舌头伸出来充满暗示地舔了舔嘴角,周围的人,由老板开始,带头鼓掌起哄。
刘玥的脸,轰一下涨红。
她不敢去具体地回忆后来发生了什么。她知道,自己挣开了双手的束缚,人也激动起来。她说她拒绝这样的游戏,老板的脸顿时变得铁青。周围有人要她冷静,可她冷静不下来,说这样就是对女员工的性骚扰,根本起不到增进团队感情的作用……
后来,老板问她:“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她热血上头,啪一下扯掉胸前的徽章,说:“是,这样的公司,我早就不想干了。”
然后,她就回到了出租屋里,在这里,待了三天。
算主动辞职,所以,只有之前做了半个月的工资,年终奖也没有。之前还听说今年年终可能会多些,能有一万,她早已计划好了怎么花:房租要留一些,大约五千。剩下一千还给同学,之前买回家的车票了,没钱了,还是借的。还剩下四千,怎么着,也得给爸妈买些东西。他们年纪都大了,供自己出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她想让他们知道,闺女已经大了,能自己担事了,不要总在老家挂念着她。
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前天晚上,爸打电话来问她,是几点的火车,哪个站,别看错了,要早些到站里去,着急些。从告诉他买好车票开始,每过两天,他都要来问问。刘玥不说,但心里知道,是他想她了。一年没见,从尺长抱到大、疼到大的姑娘,怎么可能不想。日子数着手指头过,她没敢说,她也想家。只在电话里点菜,说要吃妈做的排骨,爸包的馄饨。爸在那边笑呵呵地应,刘玥也笑。报一个菜名她心里都踏实些,闭着眼在黑暗里就好像尝到了那菜的味道,很香,很踏实。可前天,爸再问她时,她却不敢应了。
她怕了。
她突然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意气用事。不就是挤个气球吗?不就是被占点便宜吗?同事们都聪明,有老公有孩子的人也做了,只她清高,受不了折辱,于是做了出头鸟,也于是没有了钱。不仅是没钱,她工作也没了。她从毕业起就在这家公司干,听同学说过,最近的工作有多不好找,硕士毕业也才挣个五六千,还是税前。她只是个普通的本科生,离职证明老板都不会给她写句漂亮话,她要怎么办,她能怎么办?
车票钱还不起了,要钱,只能退掉,可她舍不得。她多想家啊,公司管得严,她就整宿整宿地不睡觉来熬,一夜夜地刷票。好多时候她看到有票了,困得迟钝,手就慢了一步,点进去就被抢空了,只能再守着。想让脑子敏捷些、清醒些,就掐自己大腿,总算抢到了一张。那天白天去公司,她眼下两处都是乌的。同事问她怎么了,脸都憔悴了,她就眯着眼笑。那天中午去上厕所,镜子里她都在笑。怎么能不高兴啊,抢到票了,抢到回家的票了。
给爸妈买礼物的钱也没了。她都想好了,那四千块要怎么花。不能直接给钱,他们太省,给了钱也是存起来,舍不得用。妈的手爱裂,那是冬天的老毛病,受了寒就崩开,肉里往外渗出了血。她得疼她,得给她买个护手霜,再买双好手套,好好捂捂,让妈也能养一养。爸爱抽烟,总戒不掉,又心疼钱,于是只买五块钱一包的烟,每天珍惜地拿出一根,点燃了,吸两口,再灭掉,想抽了再去点。她要给他买个电子烟,要买好的。总抽烟坏身体,更别提差的烟,平常她闻着都呛,她怕爸那肺呀,被糟践得不知成了什么样……
一桩桩,一件件,她想好了,全都想好了,只是,却都无法实现了。
她好恨自己,好悔。就算气球真破了,她碰到那男人一下,又怎么了?能掉一块肉吗?就算恶心,回来把衣服多洗洗也好了。房租也要涨了,房东年前就说过,她也没钱再租。等过了年,大冬天,她又要去哪里呢?北京真大,人也多,人挤人啊,就没了她的一块容身之处。爸前天打电话又来问她,她终于忍不住了,跟爸说,今年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
爸当时就愣了。过了好会儿才又出声。她听着电话那头呼哧呼哧地喘气,知道是爸在着急。爸着急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抖着嘴问她:“咋不回了呢?你妈排骨都买好了,馄饨皮我也擀了……”
刘玥也在抖,浑身都颤。她压了好久才压下喉咙里那股往上的劲儿。她知道,那劲儿要一出来,自己声音就要不对了。“我们公司加班。”她说:“过年,好几倍工资呢,不挣多亏啊。”
爸还没开口,妈就说话了。妈早年是厂子里的,后来下岗了,就去街上卖东西。鞋垫、毛线衣,只要能做的,她都卖。先前是嗓子喊,后来哑了,就捡了个别人不要的破喇叭,天天放在跟前播,声音大,时间久了,妈的耳朵就不太好使了。刘玥听到,妈在问爸:“怎么了?闺女说啥了?”爸捂着话筒不让声音传过去,回妈:“没说啥!”又跟刘玥说:“闺女,没事儿,你要真有事儿,就别回来,你妈那边我去跟她说。你要回来,爸妈……也都等着你。”
刘玥只应了一声,就已经有了鼻音。她赶紧挂掉电话,身边马上安静下来,黑黝黝地,像张网。儿时在家,家里也常是黑的,为了省电。但那时她不怕,有爸,有妈。黑暗里他们也陪着她,和她说话,夏天里爸还给她扇着扇,妈就拍她,一下一下。妈拍她的节奏渐渐慢了,她也就慢慢睡着了。
而现在,黑暗真可怕。像头吃人的兽,狰狞地张开嘴,要把她一口口吞掉。黑暗里没有妈和爸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啜泣声,一下一下,渐成号啕。
刘玥踏上火车的时候,是大年三十。
是她之前就买好的票,还是没舍得退。她没敢告诉爸,自己要回去。她不敢。她太累了,只想回家,哪怕只在外面看一眼,也是好。她知道,房租和工作都在催她,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这黑暗,这寂静,这万家灯火中莫大的孤独。她自私,随着春运的人流,被人群推着闹哄哄地检票,闹哄哄地上车。
车上很热,睡着了也在流汗。这是经停车,每到一处,就下去一些方言,又上来一些方言。灯总亮着,吵闹闹地,谁都是大包小包,谁都是回家过年。
车到的时候,刘玥已是一身湿汗。她的手握着包,里头没钱,也没礼物,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当年从家出来时,带到北京的换洗衣物。她斗志昂扬地走,又落魄地回。出站口吵吵嚷嚷,到处都是久别重逢、家人团聚。她心里酸,忍不住心里这寂寞,一回头——
就看见爸,还有妈,头发白了,正站栏杆外,热切急迫地朝她挥手。
妈似乎还想从栏杆爬过来,被爸止住。妈回头轻打一下爸,爸的眼角笑出一条条深深的皱纹,对妈说:“是不是我说还按着车次来等等,万一闺女回来了呢!”妈就也笑。两双被岁月侵蚀了的眼都望着她,深切,热爱。
刘玥再忍不住,猛擦一把将溢出的眼泪,捏紧手上的包,朝爸妈飞奔过去。
-

- 重新表白的话语有哪些(小心翼翼的告白的话有哪些)
-
2024-08-14 08:12:23
-

- 我是二婚,老公是头婚,每天夜里,受尽煎熬,出尽洋相
-
2024-08-14 08:10:08
-

- 火辣辣的情是什么歌名(情侣间聊天的100个话题)
-
2024-08-14 08:07:53
-

- 抖音最火扎心语录
-
2024-08-14 08:05:39
-

- 侄子上学费用全包:凤凰男重男轻女养侄子不养女儿,妻子再婚反击
-
2024-08-14 08:03:24
-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出自)
-
2024-08-14 08:01:09
-
- 西红柿清汤乌鱼怎么做好吃番茄煮紅衫魚
-
2024-08-11 16:37:29
-

- 水晶白菜蒸饺的做法窍门水晶白菜饺子做法
-
2024-08-11 16:35:14
-

- 韭菜做法有哪些韭菜做菜都有哪些做法
-
2024-08-11 16:32:59
-

- 趣知识:鸡蛋能蒸熟吗?带壳蒸蛋器蒸蛋要多长时间才熟
-
2024-08-11 16:30:45
-

- 吃什么补脾虚最好吃什么补脾虚最快最好
-
2024-08-11 16:28:30
-
- 磨牙棒和牙胶哪个好?磨牙饼干几个月宝宝能吃
-
2024-08-11 16:26:15
-

- 蒜烤鲍鱼怎么样做详细教程分享!
-
2024-08-11 16:24:01
-

- 如何制作口感酸爽的贵州酸茄子
-
2024-08-11 16:21:46
-
-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吃多长时间为宜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可以吃多长时间
-
2024-08-11 16:19:32
-
- 洒金桥小吃
-
2024-08-11 16:17:17
-

- 狗狗分娩前有哪些征兆?接生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
-
2024-08-10 23:38:11
-

- 泰迪为什么会出现下垂的尾巴?
-
2024-08-10 23:35:57
-
- 多犬家庭怎么解决狗与狗之间的冲突?
-
2024-08-10 23:33:42
-

- 小狗身起疙瘩小狗全身起疙瘩
-
2024-08-10 23:31:27



 西藏四大圣湖是哪几个 西藏的三大圣湖是哪些
西藏四大圣湖是哪几个 西藏的三大圣湖是哪些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官网)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官网)